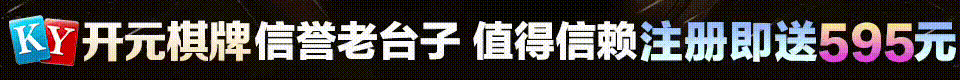PokerStars亚洲版(PS281.COM)全球最大德州扑克平台。发牌公正,与世界玩家同台竞技
捣麻糍很累,我捣过,手举一根奇门兵器般的带把大木棍儿,对着捣臼中的糯米猛捶下去,把那些颗粒分明的糯米都打醉了,醉成一团柔腻的痴迷。
与此同时,半片身子的肌肉群都得发力,而且一旦节奏上去,就像一台好不容易摇起来的手扶拖拉机,突突突地根本停不下来,直到脱力。
这个动作需要一副强健的锁骨,咳咳……
有些村子里的好汉打麻糍的兵器甚至是石头做的,我看可以排进兵器谱钝器前十,仅在宇文成都的镏金镗之下。
只可惜,这样彪悍壮汉汗如雨下打出来的麻糍,大多数地方都被做成柔腻的小吃、甜点或者干粮。女施主们撮起兰指轻启樱唇丢入,河马吃花生米一样地咀嚼一番,一两粒后就娇嗔说哎呀吃饱了呢~
搞得麻糍有时候很不尽兴。
天气一点点暖起来,等到了夏天,又可以光天化日地去小馆子里吃一盘炒麻糍。临海人尊重麻糍泡在水里的不易,所以在临海,炒麻糍是一顿猛烈正经的正餐,宜大汗、大口、大油、大盘,一顿猛造之后,四大皆空。
炒麻糍是重油猛火的典范,吃了生筋有力,这种食物就像在你肚子里结结实实地打下几堵混凝土砖墙,以框架式结构来撑起你的不会饿。早年我头一回吃就被这种结结实实的饱胀感撑住,后来一个下午在工地搬了五百块砖才稍微舒服一点。
当时一起吃的师傅倒是结棍,之后去工地,先扛个几百斤沙子上楼,然后脱了上衣抓起一把铲子伴灰,不一会儿,遒劲的肌肉上汗珠冒出,硬生生召唤回米开朗基罗的健美人体——健身房那些橄榄油怎么能比?真正的健美,都是在建筑工地上,阳光晒出来的。
中午饭点儿,戴个工地安全帽进来,拍拍裤子上的尘土,先开一瓶啤酒咕咚咕咚灌几口,然后等麻糍端上来以后大口吞食,大声开着跑堂娘姨的玩笑,骂骂咧咧地诅咒着老不付工钱的工头。伴随着锅灶上的铿锵声,煎猪油的烟绕梁不绝。
这时候,你要是文人一样体面地吃,就很不协调,没有任何理由沉默地对付一碗热烈的麻糍。因为麻糍会不爽快了,吗的老娘这么热烈的精光,你咋还不猛烈点呢?!
所以好吃的麻糍店往往都是路边摊,门口的玻璃上贴着巨大的“冷气开放”,比如著名的巾山脚下那家,店招就是老板手写。荣小馆吃过炒麻糍,总觉得是鲁智深穿着官服朝堂上作揖,隐忍一身的草莽,讲究的盘子和精细的佐料,一口口吃着,心里充满了被招安的不甘。
中国人的大部分食物就和人一样,价值观上总是喜欢内敛,把好的东西都包起来不让你看见,比如包子,水饺,又比如火烧饼,外表平淡,内里奢华,有点像闷声发大财的哲学。这和你拥有几十个如花似玉小妾的感觉是一样的,你总是不太希望人们看见,万一当中有个西门庆该咋办?
而西餐里就没那么顾虑,比如匹萨,在一块面饼上繁花似锦地堆满了所有佐料,一览无遗让你看见,甚至还担心你看不全。十八世纪的法国贵族,一听说自己老婆有人追就乐不可支,并且得意洋洋地告诉追求者自己老婆的诸多优点,生怕他们不知道正在追求一个多么完美的天使。
炒麻糍在这点上和披萨有点类似,体现着劳动人民坦诚的诉求:扎实,耐饿,佐料丰盛,一目了然,所以在气质上,炒麻糍是坦诚的、带有一些法式骄傲的。
话虽如此,我很难想象一个多情的文人能够翘着脚大嚼一盘丰溢的炒麻糍,这和林徽因抓着一只猪蹄吃的满嘴流油一样充满了违和感。要不摆一副刀叉?
节日里,家家户户都做年糕和麻糍,糯米水作,热气腾腾,晾干了之后硬如磨盘。过去人们总是把它们浸入水缸以隔绝空气,长久保存。不几天,缸水就浑浊了,漂浮着乳白色的丝滑,还有水面上几个让人揪心的乳白色的气泡,慢慢聚集起醉人的气息。我小时候打捞麻糍的时候都像是在水里摸一条滑腻肥大的黄鳝——哦不对,那是年糕,旁边像扁鱼那个才对。
捞上来之后,麻糍就像一个刚烈女子一样硬生生的看着你,这时候你一定要小心翼翼地将它清洗干净,跟它说甜言蜜语,再让它感知到你熊熊的欲火——只要一上床,哦不对是上锅煎,它就热得软糯了下来,随你折腾。
炒麻糍一般都要大汉一枚,站立热气腾腾的平底锅旁操刀——确实是操刀,因为正宗的炒麻糍唯一的工具,就是菜刀。从切料,翻炒到装盘,他就捏着一把菜刀从容不迫地排兵布阵,不晓得这个传统来自于何处。如果付账的时候店主是用菜刀接过钞票,我还能以这种彪悍对传统考究一二。
不过现在时代变了,以后菜刀上得打个收款码,与时俱进,付款的时候菜刀一翻,光亮闪过,呈现出一个二维码。店主洪钟般地说:客官,微信支付宝皆可。
像极了老弼同志。
一直觉得临海城的菜式偏北方,麦虾也是一把刀完成,紫阳街牛肉麦虾店的老太太手起刀落煮好一碗麦虾端过来,浑不似江南。
麻糍切成块,茭白、豆腐干、猪肉都切成小块,平底锅油热,铺开麻糍入锅,迅速煎起一片金黄,入佐料翻炒,料酒酱油迎头浇上,麻糍和佐料一阵欢愉,仿佛大床房上的男女,相互扑了上去,最后锅边敲开几枚鸡蛋淋上,更加抱紧的难舍难分,发出了令人精神抖擞的滋滋欢呼,与此同时,一把凶悍光亮的菜刀在它们身边翻飞挥舞,伴随全程,略带一些色字头上一把刀的哲学况味。
不一会儿,热气腾腾中,一盘炒麻糍就端到你面前。
略略煎过的麻糍带着酥脆的表皮,轻轻一咬就直探到柔软米白的内里,那温顺的绵软饱满地塞满口腔,心满意足地使劲咀嚼,顺着住喉咙滑进肚子里,慢慢消化,化成臂膀间讨生活的力气。

临海杜桥的炒麻糍和大田大排面一样出名。出名到每家小店都写上正宗杜桥麻糍二字加持。过去曾在杜桥路边摊吃过,热闹的中午,阳光下红彤彤的帐篷,满天的油烟和锅碗瓢盆相互撞击的声响,沈鸿非说四川苍蝇馆子最好吃,大约也是如此了。
多年前看汉正街的夜宵,爆炒螺丝在油锅里翻滚,佐料飞花洒落,炒好了后美丽的姑娘们端过去,闪亮的红唇饱满地吸住,玉白的腿交织着,随着大声聊天的笑声上下抖动,这种人间才有的烟尘火气,想来最是金不换。疫情看瞅着就要过去,到时候,再去汉正街,佐着长江的风月吃他一盘。
杜桥这地儿很神奇,按理说,做眼镜也算不上什么重体力活儿,却炒出了最好吃的体力活专用麻糍。这个悖论很奇妙,就像我认识一些杜桥的女施主,生意上不让须眉,闲暇时谈人生谈理想,常常地也不小心漏出一些朴素的柔情。
在这阳春三月,新绿泛上柳梢头,我想过这样的场景的:傍晚的时候,看着天边泛起令人愉悦的鲑鱼色晚霞,我披上外衣,带上门,去街上叫一盘炒麻糍吃。
东滕老街那儿有家炒麻糍老店,据说开了数十年。前次跟青青找着去吃,炉灶前却是一位老太太,刀工娴熟,难得的是柴火灶老规矩,青青城里人,见惯了精工必至的现代厨房,对柴火灶啧啧称奇,拿着手机拍这拍那的新鲜。
麻糍上桌,裹着一团软糯和气,我晓得这东西劲道,不提提神会被它撑着,所以开吃之前先来一口白酒贯通一下,阿瑞曾和我说好茶吃着,能上下贯通背脊发汗,老五说好的手冲咖啡让神志为之一明,我认真体会了一下,最后告诉他们这些感受哥们统统没有,要说贯通,还是二锅头最好,火线般奔涌入喉,唤醒五脏六腑,身体就开始活泛起来,到时候就话多,吃多,酒多,简称三多。
多少年来,下馆子都算一种待遇,酒足饭饱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一向都是理想,当年朱重八快要饿死,听说要是能黄袍加身,天天大鱼大肉,那都不叫事儿,这个念头一下子就让他斗志昂扬,砥砺前行。
如今下馆子成了懒得做饭之后的果腹,物质的极大丰富让食物唾手可得,很多老字号的坚守成了艰难的因素,地道的材料做法和讲究的慢功夫已经不容于匆匆忙忙的食客,过去临海城当年响当当的豆面碎,大人面馆,卤肥肠,俱往矣。
就像这家老店,事先交代不要味精,原味即可,吃完后回家,还是喝了一晚上的水,口渴难耐。上次和一个厨师聊天,说碰到有些食客说不要味精,他乐呵呵地说:
那就加多一点鸡精嘛!
扑克之星亚洲版6UP官方网址:https://evp89.com
6UP扑克之星官网发布页:www.6updh.com
以上资讯由GG扑克中文网整理提供!